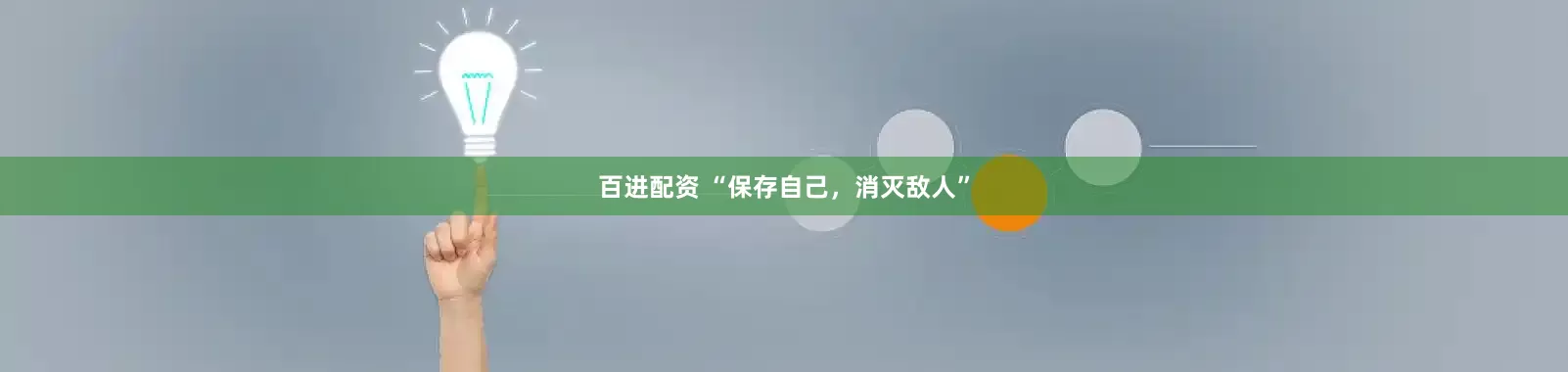

“鬼子比我力气大,端着刺刀冲我心口就过来了,我一闪,扎在了胳膊上。也顾不上疼,我赶紧来一个收枪‘防左下击’,枪托顺着鬼子的腿裆打过去,把他打晕在地,就地又给了他一刺刀!”
讲起80年前夜袭日寇的那场战斗,如今已97岁高龄的钟信虽声音有些颤抖,却目光如炬,神色中仍见当年风采。“我憋着一口气呀,一定要报仇!”
1928年,钟信生于河北省码头镇。8岁时,日军到村里“缴粮”,可老乡们本就吃了上顿没下顿,根本交不出粮食。残忍的日本兵就拿出刺刀,当场杀死了钟信的父亲。
“父亲没了,母亲改嫁,家里就剩我一根独苗了。”从此,对日本鬼子的仇恨深深地种在了这位少年的心中。
没爹没娘的孤儿,为了谋生,跑到地主家里打工扛柴,可地主不给工钱,每天发的那点儿饭,只能勉强填饱肚子。15岁时,钟信来到北京哈德门大街的一个铁匠铺当学徒,经常挨打受气。“我想投奔八路军,想打日本鬼子报仇,但不知道他们在哪儿。”钟信奔着永定河东方向寻找八路军的队伍,后来终于在朱家庄找到并参加了涿良苑西区区小队。
“区长对我很好,见我穿得破破烂烂,给了我袜子、衬衫,后来还发了军装。”钟信说,不久他便随队转到了大兴榆垡镇,那里驻扎着八路军的正规部队——冀中七十六团。
1945年8月2日,17岁的钟信正式参加了八路军,成为冀中七十六团二营四连一排一班的战士。在连长张耀武的带领下,他和战友们一起学习夜战、近身战、投掷手榴弹、拼刺刀、爆破等对日斗争的实用作战招数。“连长告诉我们,日本人有坦克,有飞机大炮,武器精良,我们要是跟他们打阵地战,就要吃大亏。所以我们就开展游击战、麻雀战、地雷战,保存自己,消灭敌人。”
投弹、刺杀,村外练兵场上,是战士们苦练的身影。“平时多流汗,战时少流血,不能怕吃苦。”连长的话,钟信至今记忆犹新。
1945年8月5日下午,冀中七十六团二营四连接到了夜袭日军防空队的任务,刚学了投弹刺杀没几天的钟信,就跟着连队前往日军防空队驻地丰台路口六圈村。“我们用的是‘夜摸’的办法,两个排掩护、一个排进攻,要快,又不能发出响动。”钟信说,出发前连长给每人发了一个贴饼子,要是咳嗽就用饼子压一压,走路要轻抬轻放,不让敌人发觉。
等大部队“摸”到了敌人防空队的跟前,对方的岗哨才发现。“我们拉响手榴弹,朝日本鬼子扔过去。他们乱成一团,吱哇乱叫,就跟猪圈一样。”钟信说,他刚学的刺杀技术,有一招叫“防左下击”,正好就用上了,这才有了本文开头那惊险的一幕。
“我们对日本鬼子都有很深的仇恨,个个勇猛。”在这场夜袭中,冀中七十六团二营四连一共击杀了22名日本鬼子,俘虏12人,缴获了九二式重机枪、步枪、“牛腿炮”等重要战备物资。
直到今天,在钟信的手臂上,当年侵略者刺刀留下的伤痕仍清晰可见。这,就是刻骨铭心的记忆!
抗战胜利后,钟信继续在一线战斗。在1947年的一场战役中,钟信冒着生命危险,炸毁了敌人的炮楼,之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他还参与了平津战役,解放了房山。抗美援朝战争时,钟信被抽调至华北军区独立二团一营机炮连任连副指导员,负责训练炮兵。
“回忆起这一生,从17岁投奔革命开始,我的青春岁月都是在军队中度过的。在党的教育下,在军队大家庭里,我学习、成长,成为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和军人。”在采访的最后,老人语重心长地寄语年轻人:“没了‘三座大山’的压迫,新时代都是幸福。孩子们不应该忘记历史,要好好珍惜现在的生活。”
更多热点速报、权威资讯、深度分析尽在北京日报App
炒股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